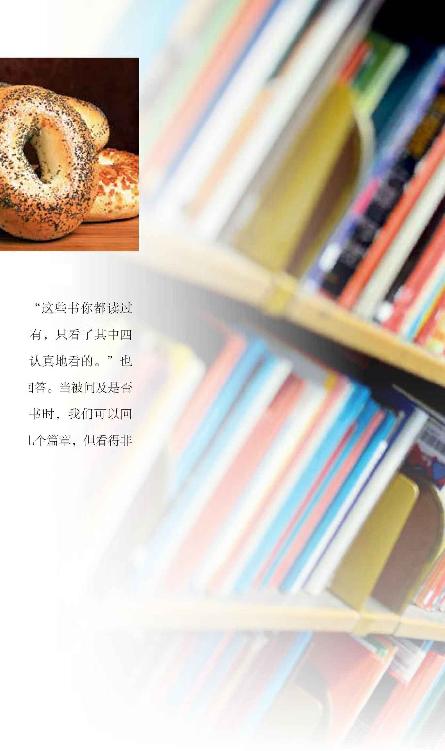书面文字

20世纪末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重新审视了索绪尔对语言如何运作的描述,并试图对其进行“解构”。
在找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区别的过程中,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在不经意中列出了有关思考的很多特征,它们在形式上是主观的、物质的和相对的,而且在口语与书面语中应用同样多。但是,口语和书面语不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只不过是哲学上的幻想。
伴随对口语和书面语区别的成功解构而来的是灵肉合一(参见笛卡儿说法)的结束。头脑对事物的认知与感觉的认知之间产生碰撞,字面意思和隐藏意义、自然创造和人类文化创造、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等对立物产生碰撞……还有更多:
“所有二元论,所有有关灵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论,以及所有一元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独特主题,而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又都是尽力抹去这些主题的痕迹。

“‘完全在场’附属的‘痕迹’在理念上得以体现,口语表达要优于书面形式,这种认为书面形式低下的想法应该进行改变。这些都是神学需要的形式,它们决定了考古学和来生论意义上的‘存在即在场,即基督再临’。生死没有区别,活着只是死亡的别名。以上帝的名义掌管生死,不过是历史的转喻。”
——《论文字学》
德里达辩称,如果语言不是处于巨大语言网络或实际生活及感知当中,就没有什么实在意义。所有一切皆是幻象,或者说是一种燃烧过后残留下来的“粉尘”。语言中还存在像“是”与“不是”的对立,以及“我”和“你”这样的词语,我们必须打破这种二元论建立的网络。
“关于‘差异性’的游戏只在合成和引用中有效,合成和引用在任何时刻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元素单独出现,而且只和自身相关。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没有一个元素不与其他元素发生联系就能够单独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元素本身不能单独简单地存在。
“这种交互作用就像‘织布’,一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转化而来的。无论元素之间还是系统之中,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简单在场或缺席。痕迹和延异无处不在。”
——《符号学与文字学》
但是,人们很难理解德里达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是先验事物呢?德里达本人喜欢提出问题,却拒绝进行解释。在各种场合,他都坚称,解构本身不是一种方式,也不是一种表现形式,而是一门学科中的某篇文章。事实上,他曾经在“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信”中称,绝不可能说“解构是如此”,也不能说“解构不是如此”,因为“句子结构是如此”这样的结构本身就是错的。
有一点需要肯定,哲学家善于创造新术语,却拒绝接受他人对这个新术语做出的任何解释。德里达承认曾经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揭露西方文明和普遍“人性”的破灭,他有一个早期哲学课题,称为“Dekonstruktion”(解构)。为课题目标,海德格尔借鉴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例如,他从另一位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那里引进的“超验现象学”。这个术语来自纳粹精神病学杂志,据说这本杂志是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的表弟主编的。

说起海德格尔,不得不提及他曾经长期参与纳粹党的工作。不管怎样,海德格尔的研究还是值得关注,他强调并质疑了,在我们构想世界(在我们的思想和书写的文字中)时,时间担当的角色。
从海德格尔及其解构中得到启发,德里达也采用了“在场”(presence)这个词。海德格尔在谈及“存在”(being)这个概念时用到这个词,在谈到“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异”)时也有所提及。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把“差异”定义为“存在论差异的前奏”,也间接提到过这一观点。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的哈佛大学,1956—1957年,德里达曾经在这里学习。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的哈佛大学,1956—1957年,德里达曾经在这里学习。
看看德里达的著作,很少有原创作品,也许根本不值得用心去读。如果你对读他的书缺乏勇气,那就去看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电影传记吧,这部影片叫《德里达的故事》,2002年上映。这部影片把德里达描述成一个滑稽角色,就像“我们中的一员”。他的犹太人出身从他的早餐百吉饼中可以看出。他具有自我怀疑性格,总是担心自己的衣服颜色是否协调。
当摄影机随着他进入图书馆时,我们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书摆在书架上。记者问德里达:“这些书你都读过吗?”他回答:“没有,只看了其中四本,但我是很认真很认真地看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如此回答。当被问及是否读过德里达写的所有书时,我们可以回答:没有,只是看了几个篇章,但看得非常非常仔细。
 百吉饼是哲学家的早餐。
百吉饼是哲学家的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