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内在二重性例证
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我们可以举一些事实来表明这种区别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是不能缩减的。
拉丁语的 crispus“波状的、卷绉的”给法语提供了一个词根 crép-,由此产生出动词 crépir“涂上灰泥”和 décrépir“除去灰泥”。另一方面,在某一个时期,人们又向拉丁语借了 dēcrepitus“衰老”一词,词源不明,并把它变成了 décrépit。确实,今天说话者大众在 un mur décrépi“一诸灰泥剥落的墙”和 un homme décrépit“一个衰老的人”之间建产了一种关系, 尽管在历史上这两个词彼此毫不相干:人们现在往往说 la facade d écrépite d’une maison“一所房子的破旧的门面”。这就是一个静态的事实,因为它涉及语言里两个同时存在的要素间的关系。这种事实之所以能够产生,必须有某些演化现象同时并发:crip-的发音变成了 crép-,而在某个时期,人们又向拉丁语借来了一个新词。这些历时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同它们所产生的静态事实并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不同秩序的事实。再举一个牵涉面很广的例子。古高德语 gast“客人”的复数起初是 gasti,hant“手”的复数是 hanti,等等,等等。其后,这个 i 产生了变音(umlaut),使前一音节的 a 变成了 e,如 gasti→gesti,henti→henti。然后,这个 i 失去了它的音色,因此 gesti→geste 等等。结果,我们今天就有了 Gast:Gste, Hand:Hnde 和一整类单复数之间具有同一差别的词。在盎格鲁·撒克逊语里也曾产生差不多相同的事实:志初是 fōt“脚”,复数*fōti;tō“牙齿”,复数*tōi;gōs“鹅”,复数*gōsi 等等。后来由于第一次语音变化,即“变音”的变化,*fōti 变成了 fēti;由于第二次语音变化,词末的 i 脱落了,
*fēti 又变成了 fēt。从此以后,fōt 的复数是 fēt,tō的复数是 tē,gōs 的复数是 gēs(即现代英语的 foot:feet,tooth:teeth,goose:geese)。
从前,当人们说 gast:gasti,fōt:fōti 的时候,只简单地加一个 i 来表示复数;Gast:Gste 和 fōt:fēt 表明已有了一个新的机构表示复数。这个机构在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古英语只有元音的对立,德语还有词末-e 的有无;但这种差别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单复数的关系,不管它的形式怎样,在每个时期都可以用一个横轴线表示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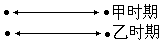
机反,不管是什么事实,凡引起由一个形式过渡到另一个形式的,都可以置于一条纵轴线上面,全图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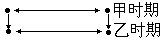
我们的范例可以提示许多与我们的主题直接有关的思考:
- 这些历时事实的目标绝不是要用另外一个符号来表示某一个价值: gasti 变成了 gesti,geste(Gste),看来跟名词的复数没有什么关系;在tragit→trgt“挑运”里,同样的“变音”牵涉到动词的屈折形式,如此等
等。所以,历时事实是一个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的事件;由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特殊的共时后果,那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
- 这些历时事实甚至没有改变系统的倾向。人们并不愿意由一种关系系统过渡到另一种关系系统;变化不会影响到安排,而只影响到被安排的各个要素。
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一条已经说过的原则: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 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象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和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会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要表示复数,必须有两项要素的对立:或是 fōt:*fōti,或是 fōt:fēt;两种方式都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可以说未加触动就从一个方式过渡到另一个方式。变动的不是整体,也不是一个系统产生了另一个系统,而是头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了,而这就足以产生出另一个系统。(3)这一观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状态总带有偶然的性质。同我们不自觉地形成的错误看法相反,语言不是为了表达概念而创造和装配起来的机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变化出来的状态并不是注定了要表达它所包含的意思的。等到出现了一个偶然的状态:fōt:fēt,人们就紧抓住它,使它负担起单复数的区别;为了表示这种区别,fōt:fēt 并不就比 fō t:*fōti 更好些。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在一定的物质里注入了生机,使它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这种看法是历史语言学提示给我们的,是传统语法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用它自己的方法永远得不到的。大多数的语言哲学家对这一点也同样毫无所知,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这是最重要不过的。
- 历时系列的事实是否至少跟共时系列的事实属于同一秩序呢?决不,因为我们已经确定,变化是在一切意图之外发生的。相反,共时态的事实总是有意义的,它总要求助于两项同时的要素;表达复数的不是 Gste,而是 Gast:Gste 的对立。在历时事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它只涉及一项要素; 一个新的形式出现,旧的形式(gasti)必须给它让位。
所以,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将是一种空想。在历时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
现在再举一些例子来证明和补充由前一些例子中所得出的结论。
法语的重音总是落在最后的一个音节上的,除非这最后一个音节有个哑 e。这就是一个共时事实,法语全部的词和重音的关系。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以前的状态来的。拉丁语有一个不同的、比较复杂的重音系统:如果倒数第二个音节是一个长音节,那么,重音就落在这个音节上面;如果是短音节, 重音就转移到倒数第三个音节。这个规律引起的关系跟法语的规律毫无类似之处。重音,从它留在原处这个意义上看,当然还是同一个重音;它在法语的词里总是落在原先拉丁语带重音的音节上:amcum→ami,ánimam→me,然而,两个公式在两个时期是不同的,因为词的形式已经变了。我们知道,所有在重音后面的,不是消失了,就是弱化成了哑 e。经过这种变化之后,重音的位置从总体方面看,已经不一样了。从此以后,说话者意识到这种新的关系,就本能地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甚至在通过文字借来的借词里
(facile“容易”,consul“领事”,ticket“票”,burgrave“城关”) 也是这样。很显然,人们并不想改变系统,采用一个新的公式,因为在 amcum
→ami 这样的词里,重音总还是停留在同一个音节上面;但是这里已插入了
一个历时的事实:重音的位置虽然没有受到触动,却已经改变了。重音的规律,正如与语言系统有关的事实一样,都是各项要素的一种安排,来自演化的偶然的,不由自主的结果。
再举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古斯拉夫语的 slovo“词”,工具格单数是 slovemъ,主格复数是 slova,属格复数是 slovъ等等,在变格里,每个格都有它的词尾。但是到了今天,斯拉夫语代表印欧语ǐ和ǔ的“弱”元音ь 和ъ已经消失,由此变成了例如捷克语的 slovo,slovem,slova,slov。同样,ena“女人”的宾格单数是 enu,主格复数是 eny,属格复数是 en。在这里,属格(slov,en)的标志是零。由此可见,物质的符号对表达观念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例如在这里,人们之所以知道有属格复数的 en,只是因为它既不是 ena,又不是 enu,或者其它任何形式。像属格复数这样一个特殊的观念竟至采用零符号,乍一看来似乎很奇怪, 但恰好证明一切都来自纯粹的偶然。语言不管会遭受什么样的损伤,都是一种不断运转的机构。
这一切可以确证上述原则,现在把它们概括如下: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
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每个变化都会对系统有反响,但是原始事实却只能影响到一点,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前后相继的要素和同时存在的要素之间,以及局部事实和涉及整个系统的事实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使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一门单独科学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