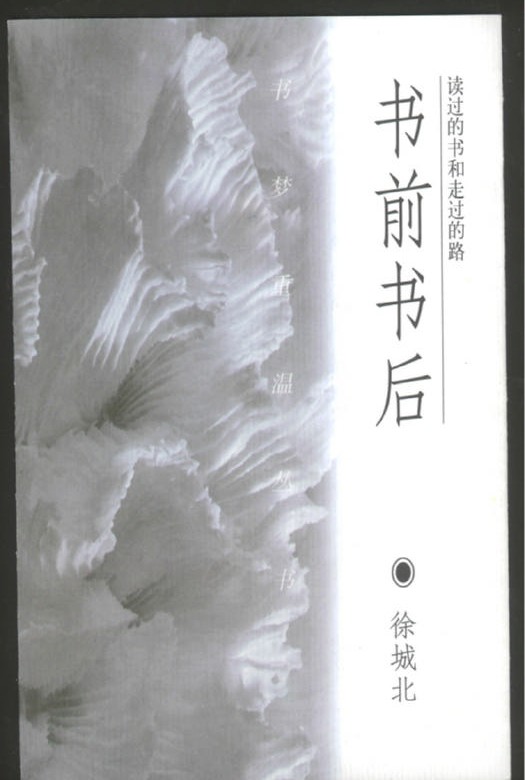
书前书后
《青铜器图释》
60 年代初期,我一度失去了“单位”,形势危急,十分的苦。
今天的青年人听了——那又有什么!不怕没“单位”,就怕没本事! “单位”不合适,还可以辞去了另找!今天的个体户不都是没“单位” 么?下岗的人不也没“单位”么?
那年月可不是这样。每个城市居民都要同时受到两层管辖。一层是户籍,就是你住在哪里。得让管“片”的民警承认和管理你。二是要有自己的“单位”。学生要有学校,在校学生有病可以休学,千万不能退学,一退就没“单位”了,一没“单位”就没“合法身分”了,以后再想求学求职就难了。
那时,我就碰上这倒霉的第二条。 1960 年我高中毕业,挺好的成绩却只考上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属二类学校,但总算是四年制。这个学校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一切白手起家,简陋之极,我很不高兴。刚上没几个月,就赶上院系调整,学院就动员一批身体不太好的同学休学,其中有我,因为体检表上注明中学时代有心脏病,体育免休。我没犹豫,休就休吧。心想正可以准备一下功课,明年另考一个好大学。第二年,休学期满,学院已并入北京师范学院,后者则动员我退学。父亲找到学院去问——是不是因为双亲被打为右派的缘故。回答否,只说院系调整,学生名额多了,一定要减。校方还举例说,和我同班有一个病歪歪的干部子弟(女生),同样也得退学。父亲没话,回来了。我本来也不太“在意”这学校,就办了退学手续。可后来没多久,学院就又把那女生“请”回去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幕,她完全就是一个“托儿”。
且只说我。一回家,表面上再没人管我了,可实际不然,民警会时不时进家找我“谈话”。当然,态度是客气的,只是问问平时的生活安排,并不问我对未来的工作设想。那年月找工作很难,如果街道上分配到去某工厂的名额,那真像一块香饽饽,多少人争啊抢的。最后,也只有那些出身好而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的青年,才轮得上入选。
对此,我则不屑一顾。对于前途,我是既坚定又茫然。说坚定,则一定要干“文化工作”;至于到底干什么,则又心中无数。沈从文伯怕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对我父母说:“弟弟(他总这么称呼我,我父母也这么称呼他的儿子)应该抓紧年轻的时候多学些文化,否则年纪一大, 就记不住了。”于是,我一度全面开花——诗词、国画、京剧⋯⋯什么都来,到处“拜师”。搞了一段,心里也没了主意,父母遂又问计于沈。
沈对我父母说,“问问弟弟,愿不愿意跟我学文物研究?” 可文物的范畴也太宽泛了。
“那么,不妨从青铜器的欣赏和鉴定入手,就先看一些这类书吧。” 沈开列了一长串书籍名单,有铅印的,也有善本的。沈还向我父母
说,“弟弟古文不错,能看没有标点的古书;听得懂我的湘西话,看得懂我的毛笔字。如果要干,就要趁早,趁我现在还有挑选助手的权利⋯⋯”
于是,我拿着这份儿书单,每天骑车到北海旁边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一去就是两个半天,因为中午回家吃饭。把书包存在门口,只带笔
记本和一个喝水杯子进去。
我连看了一个月。那时脑子真是好使,书上的文字并不难懂,只是太枯燥,读得我痛苦不堪。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了“文化”和“文艺”的区别。敢情我的性情是倾向艺术的,我倾倒于热闹和疯狂,而不堪于研究文化的坐冷板凳。
我转而注意图书馆中的其他读者,绝大多数都有“单位”,他们按时来也按时走,他们看书是分内的工作,看多看少一个样,快看慢看一个样,闭眼睛休息也同样挣工资。
但我发现期刊阅览室中有一位不肯按时走的读者:姓陈,男性,年纪 20 岁上下,驼背很厉害,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一早来,闭馆才走, 中午都不回家。他每天借阅各种新到期刊中的文艺作品,不断给各种期刊投稿。投中的不多,且“块头”很小。
我和他渐渐认识了。他奇怪我为什么要读青铜器的书。我如实以告, 他摇摇头:“太苦了。”
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现在先发表些小文章,将来到报社、杂志社当编辑。”
我去了他的家,就在府右街的南段路以西的胡同里。家境并不太好, 给他在院子里单盖了一间简易房屋,10 平米,一尘不染。作为男性,也有些洁癖了。
我整天看青铜镜(沈要我集中到镜子上来),同时也看他——应该说,他是我的“又一面镜子”。他的确是苦,可我又何尝不苦?如果我跟随了沈伯怕,大约此生就要每天如此机械地生活
我犹疑起来,更痛苦起来——母亲发觉了我的情绪变化,让我有什么话直接找沈伯伯说。我去了,沈问我“还读得进去么?”
我不说话,是不能回答。
当时是夏天,沈的那间小屋子太热,吃完晚饭,他和我并排坐在他的门口,那里可以看见一角天空。他说:“你看,天上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这颗是茅盾,那颗是巴金,又一颗是老舍⋯⋯”
我知道解放前在国统区有一个“四大作家”的说法,除了上边三位, 最后还有他。我问:“您在哪儿呢?”他举起那只小而胖的手,摇了摇说:“早没有了,我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当说明员,就很好。真的,要想当好说明员,还不容易呢⋯⋯”
沈伯伯自一解放就改换了他的工作,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可我, 学了半天青铜镜,可镜子中却照不见我的人影⋯⋯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上大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中给我借回这部书,英汉对照,上下两本,根据莎士比亚 20 个戏剧故事改编的散文。我打开到英语部分反复“相面”——是吗?⋯⋯不错,它就是!但当年不叫这个名字,且翻译者不是我所熟悉的萧乾伯伯。萧译于解放初期,此前它还有几个译本,名字都很怪,有的叫《澥外奇谭》,有的叫《吟边燕语》,然而我在 60 年代初期读的,只有英语部分,汉语书名被称作《莎氏乐府》。
它的文字比较古典,句子往往很长,时常要由五六个分句和一个主
句组成。主句短小,不显眼,喜欢隐藏在某个角落,你不留意还真找不到它。分句则又长又漂亮,词汇比较古雅,用老辞典才找得着。文法更是复杂,绕来绕去,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我已不记得是从哪儿搜罗出来, 一看就满心欢喜,于是试读了一两篇。发现难度颇大,便带着它去找我的英文老师张友松先生。
张先生是老资格的英语翻译,好像和曹靖华同辈。他主要翻译马克·吐温的作品,1957 年获罪,被戴上右派帽子。他原先是“有”工作的,但经过了 1957 年,不知怎的就没了工作——不知是自己辞去的呢, 还是被组织上开除的呢?反正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起,他就成了专业翻译当中的单干户。反右之后,不允许他用原来的名字翻译书了,几经商量, 他便有了一个笔名“常健”。他曾经要求恢复他的公职,但一直被搁置, 于是他每翻译出一部书,便拿一笔稿费。他和他不工作的太太就靠这活着。在 60 年代前期,国家的外文翻译任务就少,哪儿就轮到了要他去翻译?再说,即使让他翻了,即使书也出了,稿费的发放也要过些时日, 哪里能今天出书明天就支稿费?可他和太太都要吃饭啊!他为此常常发脾气,时常为发稿费的问题和社里吵架。要是一般人还好说,可他是右派,居然也脾气挺大,结果弄得社里挺烦他。他总和周围的关系搞不好。他说他想搞好,但总是没搞好。
他和我父母很熟,什么时候熟的和怎么熟的我都不晓得,但让我在学戏之余还学英文,是母亲的主意。她说:“多学点没坏处。我当初来北京上大学,就学的是英语。后来搞新闻去了,虽说基本上放下了,可遇到偶然情况,比如抗战中去张家口,是和几个美国记者一块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去的。机舱挺小,装不了几个人儿,我就在机舱中用英语和他们对话。他们很惊奇,惊奇中国记者也能会英语,于是很佩服我也很敬重我。”
我说:“学京剧还学英语干什么?难道要用英语唱戏?” “出国唱戏时,会点英语总没坏处。” “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干京剧呢!” “先别管到哪儿干,乘现在年轻先学着,没坏处。等老了,想学也
学不动了。”
“⋯⋯”
尽管我始终“保留意见”,但母亲就一意孤行起来,她去到西城缸瓦市找到张先生,要他每周教我三次英语。他们是熟人儿,一说就妥。第一次登门,是母亲陪我去的。自第二次开始,我就独往独行了。
张家住在缸瓦市以东的一条胡同里,张先生住的是三间北房。张家就老两口。张的书桌上有一个倾斜的木板,那上边是他的稿纸——译稿,木板旁边是几部摊开的大辞典,他随时用得着。图个方便,一伸手就“够得着”。他教我是在饭桌边,教材都是他选的通俗故事。本来我建议用
《北京周报》,他不同意:“太政治化,英国人平时哪儿用得着。再说, 都是中国式的英文。”他不教我会话,而着重在笔译。“我是翻译,我的会话就不好,你学英文不会是当口译,学点笔译,无论用不用,总没坏处。”
“总没坏处”——这口风跟我母亲挺相似,说不定就是我母亲灌输给他的。但师道尊严,人家准备好的教材,自己总不能不念吧?
他生活中有些怪僻。冬天睡觉嫌被子沉,便用粗铁条弯了一个半圆形的拱架,放在床单上。晚上睡觉,他睡在床单上,上边是这铁条弯成的拱架,被子再放在拱架上。这一来,保暖依然保暖,被子却“压”不着他了。他家还养鸡,可每天关在笼子里,从不放风。久而久之,母鸡就下了软壳的蛋。张先生也不着急,就出去从缸瓦市的西药房买了些钙片,用它喂鸡,果然蛋壳就硬了。为此张先生特得意。
我跟他学了好长时候的“英翻中”,但词汇量没多出多少,倒是中文的嵌词造句提高了不少。我不敢公然反对老师的教法,于是婉转建议“丰富”一下教材。我用了“丰富”一词,老师没留意,顺口回答:“你自己也找找吧。”
我找了,找的就是《莎氏乐府》。
我带着《乐府》去见老师,一看原文是“看”过的——每个生词旁边,我都用红笔注了音标。
“看来,我挺喜欢这种英文的。” “它的句势复杂,分析清楚了,再难的文法也不怕了。”
张先生没多说什么,给我耐心地解释。但他后来在学习完的闲谈中讲,“我不反对《乐府》,但主张你现在不要太迷恋它。学英语,不在乎用多少生涩的单词,关键倒是那些常用词,通常一个词会有许多种用法,你得一个个都能分辨清楚。这最难⋯⋯”
张的个性很强,他教我不但不收学费,反而还“倒贴”。每次我去学的那个晚上,他都预先从东城一家专卖西式点心的铺子买来“洋点心”,以备教完之后闲谈时品尝。我这人不客气,但对他也有些敬畏。他讲的道理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以后就没有再钻《乐府》。
后来我去了新疆,和他一别多年,再没有见到。只知道他“文革” 初期很受了些苦。大约是出版社中有人批他传播“封资修”(重点是资和修),他不服,并且和人动手打起来,结果后来闹了个头破血流。大约很久很久之后,曾接到他一封发自成都的信,讲自己 50 年代遗留的问题至今还遗留着,如今是和儿子住在一起,也不去想它了。
他寄这封信时已 80 多岁了,如今很长时间没通音讯,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我默望南天,祝愿这位虽有怪僻却心地善良的老人晚年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