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喜爱的诗人
——莎士比亚[1]、埃斯库罗斯[2]、歌德[3]
上述三位名人,好似不同历史纬度上出现的三大群岛,对于自幼心灵就充满沸腾诗情的马克思来说,恰似为那浩瀚的诗海标志着几条象征性的界线。现代诗有其地理的轮廓。在东方,普希金达到最高峰,在西方,升起惠特曼之星——好像《宇宙的精灵》,在他的《草叶集》的絮语声中。从荷马笔下那些半神话的有着英勇果敢品质和人类社会生活朴实传统的希腊人,直到一排排站在阶级风雷中威风凛凛地放声诅咒“耳聋的上帝”、“富人的国王”、“虚伪的祖国”的那些西里西亚织工们[4],一群典型形象簇拥而来,浮在眼前。
亲近的人都深知,马克思富有“无可比拟的诗意想象力”,诗歌就是他创作的摇篮,他的第一篇文学试作就是诗。精心保存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六本笔记,是他的处女作《爱情集》和《诗歌集》。少年马克思的诗才,是用哲学抒情诗语言表述的,笔记中献给卓越的思想家黑格尔、歌德、席勒的诗为数不少。他乐意编写叙事诗,锋利似剑的题铭诗和无畏奋战的悲剧诗。但是更充分、更明朗地表达他整个身心的还是那一首首《致燕妮》的十四行诗。
燕妮!笑吧!你会惊奇:
为什么我的全部诗篇,
只用一个题目:《致燕妮》?
那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安慰之神,
使我的心儿豁亮到底。
你所有的美,都凝结在你的名字里。[5]
…………
然而,甚至在最发狂的浪漫主义激情之下,诗人马克思被思想家马克思制服了:真的,你的艺术“也并不像燕妮那样美丽”,看来,你以“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有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只蕴藏在致燕妮的诗中,而且这些诗失掉了必要的精炼,变成了模糊不清的东西……
如果燕妮“含着爱和痛苦的眼泪”读到马克思的那些诗,并以某种隐匿的心情终生珍藏着那些献给她的笔记,那么,马克思自己,用他女儿劳拉的话说,“对待这些诗是极不尊敬的”。这些诗他当然不是为了“去发表”。有些诗在他逝世之后,几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问世,而绝大多数的诗,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大约经过一个半世纪才为我们所知。
诗并未使马克思成为显赫的诗神,却留作他永恒的伴侣,它不仅把马克思那犀利刚劲的文笔缠上了芳香的花环,而且以一种特殊的磁力,把许多现代诗界巨匠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伟大的富有戏剧性矛盾的海涅、朴素的有“铁百灵鸟”之称的海尔维格、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阵风的无产阶级政论家维尔特、有才华但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弗莱里格拉特[6]以及符佩尔塔尔的朴实的小伙子西倍尔,等等。
那么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这三个亲切、喜爱的名字并列一起,原因何在呢?
三位伟人中的歌德几乎跟马克思同代,属现代人。歌德在魏玛去世时,马克思已在特里尔中学上学了。歌德比马克思只大四分之三世纪,莎士比亚却大两个半世纪,而埃斯库罗斯则大两千多年……然而马克思出于对诗的爱,把他们如同一个大家族般地连在一起了。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那永不停息的对生活真理的追求,是那对“真正人类本质的理想生活”的探索。这点,经常不断地、深深地打动了马克思。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智慧,不在于只使每个人在本世纪内成为时代最响亮的扩音器,而在于他们去暴露和反映“合理关系”的本性,使非人的世界人道主义化,有助于未来的生活改革者去认识苦难人类的存在,人类是会思维的,而且会思维的人类正在受着压抑。马克思把不同世纪的三位酷爱真理的泰斗相提并论,是想了解以往那些在绚丽多彩的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千年来所有的真理,并在自己的心目中把它串联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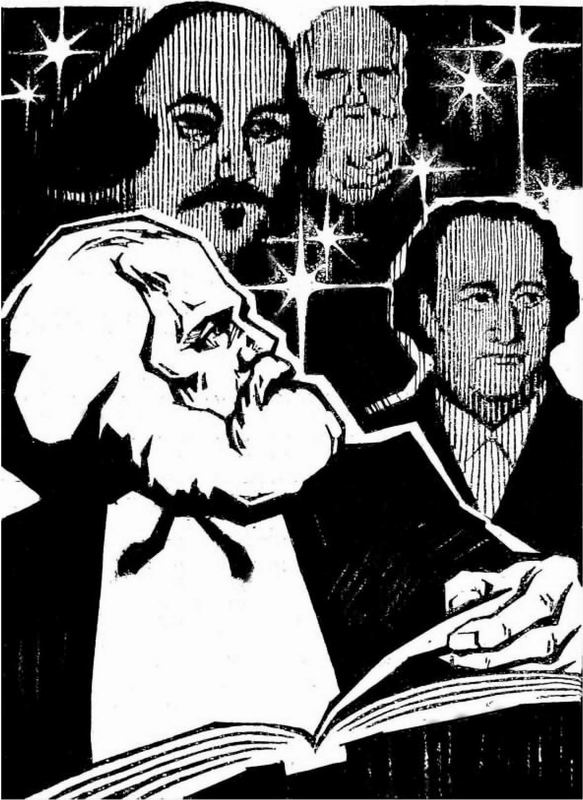
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世界史,是位最伟大的诗人!”有一次,恩格斯把海涅的诗寄给朋友,如同寄送那些令人震惊的政治新闻一样,在信中赞不绝口地说道。
千真万确啊!在历史的舞台上,在那些最突出的形象和鲜艳的颜色之中,在那些强烈的情感和激情的狂热交织之中,在那些意外而紧张的活跃动作之中,常常渗透出一些深刻的现象和重大的事件。无论是“会思维的头脑”,无论是“具有强烈情感的心”,都参入世界艺术的开发。诗人的语言,不仅有生活真实,历史的事件,而且带有不朽的精神价值。诗是按其“美的规律”在创造。然而一个真正艺术家,是不会违背生活真实的规律,他只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情感去丰富历史的事实。
马克思与黑格尔那种绝对地把世界艺术的开发移到次要地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艺术是充实人的智力的一种最丰富的宝库。毋庸置疑,艺术是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无论如何它不亚于其他的形式,这一点他坚信不疑。重要的只在于使自己懂得艺术创作的本质和规律,才能使形象语言轻易地译成历史真实的语言。
马克思完全掌握这种“翻译”的才能,从他早期的科学著作起就给人以典范,就是说,能从交织在艺术作品里的那些非理性的思维中找出社会历史的真谛。至于受到马克思热爱和崇敬的世界诗坛的三位伟人,无疑更是最有声望的导师。根据他们的诗,马克思同样能研究人类多灾多难的过去。
然而对他们的评价不只于此。他经常关注他们的作品,为的是欣赏诗的复调音乐[7]、思维的博大宽广以及他们诗作中的悠远的情调……是单纯的欣赏吗?!若是一个人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材料,循序渐进地了解到走锭精纺机、机车、电报和金融银行时代的资本主义屠杀人类的暴力,——难道这个人能够满意赫尔墨斯和丘必特[8]的社会,或者甚至说福斯塔夫[9]、浮士德的社会吗?……须知,这一切都是昔日时光的阴影,是世界在它童年镜子里的一种反照,更为成熟的社会的艺术,应当是富有强烈的魅力。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
但艺术向成熟方向发展就没有规律了吗?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相比。”[11]
马克思毅然抹掉他所选择的诗歌先驱者们这种“年龄上”的差别,已过去一世纪和一千年的悬殊,所以“看上去”他们只比“红色博士”[12]本身“大一些”。他一心一意地相信他们的经验、智慧和心灵,在他们那些给人类以聪慧的教导之中,为自己的世界观找到知音并借助于他们来检查自身的道德标准和原则。他们志同道合:26岁的马克思,“100岁的”歌德,“280岁的”莎士比亚……是诗歌铺开了学者思想的道路,并加之以桂冠。让我们听听他们关于财富的无限权力和金钱的变态力量的争论吧。
马克思: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13]
歌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像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14]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15]
这是他们发出的独白。而被这些独白迷住了的马克思博士,已用自己的科学语言把歌德的思想重述一遍。而在暴露独白在货币上是自相矛盾的、颠倒事物本质的特性之后,把莎士比亚的话又作了归纳,由此引出一个新的结论:这种颠倒是对抗性的,它不能成为永久的规律。于是年轻的思想家便运用预言性的独白:
马克思: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16]
这是《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一段话——这些不过是伟大诗人们有助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片断。马克思著作中援引诗人话语的地方很多。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若找到没有他们名字的一卷是很难的。而且他们处处以研究人学的大权威、历史的活见证人、沙场上的战友出现。如果说在全集里见到古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名字尚有十几次之多,那么见到莎士比亚的名字则不下于150次,歌德的名字几乎也是如此。他们仿佛在马克思语言的整个体系、整个文化财富之中,都渗入了自己的良好影响,增添了艺术上如花似锦的色彩。马克思那文风、笔调为我们作了补充的说明,恰好是他从诗海里把这三位诗人捧了出来之所在,因为他敬仰他们的文学体裁富有哲理性,戏剧的紧张性,众多的形象性和人的强烈情感性。
大概连马克思本人都不可想象他的记忆能容下如此大段大段的诗句。许多诗的形象、比喻,似乎都融化在他的演讲里,在他的笔下生辉。歌德的诗句,正如拉法格所说,马克思能背诵如流。“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做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17]
首先谈谈埃斯库罗斯。用—个最有说服力的形象来说,那就是马克思在从事最初科学著作时,总是离不开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自我牺牲反对神的暴虐的战士形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博士论文献给亲爱的老朋友——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反动怪影阴暗面前从未畏葸恐惧”,总是“以满腔的热情、严肃的态度、固有的真理”拥护着进步,百般称赞年轻马克思的才华,并培养他具有一种审美能力,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那种求知的兴趣。
埃斯库罗斯的古典悲剧形象逼真,在人物和场景方面虚构出古希腊罗马社会,把原始时期的社会斗争的经验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他从中能领悟到古希腊罗马的反抗斗士的人道主义思想、目标和功绩的意义(《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第一个人民政权的教训(《七将攻忒拜》);能够研究古希腊的家庭社会学(《俄瑞斯忒斯》)。[18]埃斯库罗斯所倡导的人的团结思想为马克思所理解而且甚合其意。甚至在结束学业之后多年,与他的朋友火热的革命者约翰·贝克尔促膝相谈时,他意外地提起埃斯库罗斯的一段话:“应当极力去开发世界上的财富,以便帮助贫困中的朋友!”而且他还指出他们具有渊博的才智和他们近似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观点。
业已跨入40岁的马克思在阐述古代的无比杰作的魅力时,论证说:
“—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9]
再谈莎士比亚。他的名字,马克思自然会把它摆在第一位。他们是两位泰斗,彼此是那么相近。马克思不仅十分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自己的思想同他也是十分相通的。诗人的戏剧和悲剧不只是历史化身的画面使马克思感到兴味,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莎士比亚的戏剧能“体现绝对性格的概念”。而这些作为“绝对粒子”的性格是用马克思思想结构中的建筑材料制成的。马克思在“莎士比亚化”,甚至是通过人的情感在揭露最抽象的,似乎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同资产阶级理论家论战着的马克思,有一次一边嘲笑一边埋怨他们说,即使两个半世纪前的莎士比亚也比他们对货币本质的了解要清楚得多。正当他最后精心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他把伟大的诗人当做自己的可靠盟友。
让我们再翻开《资本论》来看看吧。其中,在那种种事实的清晰结构中间,在那展开的提纲与精确定义的科学公式中间,我们会突然遇到《亨利四世》剧中曾击败过福斯塔夫的机灵寡妇奎克尔,我们会听到喜剧《无事生非》中西柯尔的警吏——好心人道勃雷的教诲,我们会看到《威尼斯商人》剧中夏洛克那对贼溜溜的目光,我们还会听到雅典的泰门把金子的力量奉若神明的独白。
马克思的语言研究者们,把马克思著作中所引用过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编成一个独特的人物表。首位当属福斯塔夫,他多半在马克思的“活动戏剧”前台上出现。继他之后是夏洛克、雅典的泰门,然后是《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剧中的人物;还有一整串的喜剧典型人物:阿雅克斯和忒西特、木匠斯纳格和织工奥斯诺娃……
可见,莎士比亚不仅以对现实的亲身领会和对人的个性的深刻研究在“帮助”马克思,而且还用讽刺形象的整个武库在装备着他。马克思出色地运用独有的讽刺性的比拟,写出莎士比亚化的战斗散文,弹无虚发地向敌人进击。
每当谈起这位英国大戏剧家在马克思家里占统治的地位时,马克思的作传人和研究者们便都友好而欢快地发出“崇拜”一词。是的,马克思所有的三个女儿都把莎士比亚称为喜爱的诗人。小女儿爱琳娜,甚至在六岁时就能背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大段台词。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在家长的积极影响下,形成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热烈赞扬者和精明鉴赏家的独特俱乐部,是很自然的。除马克思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之外,常来参加莎士比亚作品朗诵协会的还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剧作家艾德华·罗兹,女演员捷奥多拉·莱特,女作家多莉·雷德福及其丈夫、法学家、诗人亨利·尤塔。玛丽安娜·科敏也是“道勃雷俱乐部”的参加者,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是以喜剧《无事生非》剧中人物命名的。科敏记得自己首场演出会上还曾扮演了马克思所喜爱的《约翰王的生与死》一剧中的王子的角色。朗读之间,她一眼就瞥见长着长长的蓬松的灰头发、毛茸茸的灰胡子,一对敏锐的闪动着幽默目光的黑眼睛的马克思在全神贯注地听她朗读。他坐在带壁龛的长房间的顶端,他身后,屋角的台座上摆着一个丘必特的半身雕像,许多人公正地认为他们之间何其相似啊……
除这个家庭朗读会之外,“道勃雷俱乐部”成员在伦敦的“里采乌姆”剧院莎士比亚演出会上经常露面。他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地去提高伟大剧作家的声望。如果说,马克思家中的年长者总是拿起笔去捍卫莎士比亚的荣誉,那么家中最小的爱琳娜,成为英国莎士比亚学著名学派中的一名得力门生,也是不言而喻的。
甚至根据恩格斯的一篇著作“风景”中的片断,便能想象出莎士比亚作品在“道勃雷俱乐部”协会里是多么令人感到亲切、理解而且就像身临其境似的。
恩格斯富于幻想般地赞美着说:
“啊!不列颠内地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诗意啊!你常常会觉得自己是生活在欢乐的英国的黄金时代,觉得自己见到莎士比亚背着猎枪在灌木丛中悄悄地寻找野物,或者你会感到奇怪,在这块绿色草地上竟然没有真正演出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妙的喜剧。因为不管剧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在法国,或在纳瓦腊——其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基本上总是欢乐的英国,莎士比亚笔下古怪的乡巴佬、精明过人的学校教师、可爱又乖僻的妇女全都是英国的,总之,你会感到,这样的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20]
最后谈谈歌德。马克思在这位“德国伟人”的诗的熏陶下产生多少思想感情啊!未来思想家增长智力,就像幼苗贪婪地吮吸大地乳汁一样,首先要去汲取祖国文化当中生机勃勃的力量,汲取它思想方面的最强流。亲爱的读者,假如在我们的童年时代《俄国诗歌太阳落了》,那我们一生就要在它的反光下度过。马克思在14岁前是生活在“歌德的时代”,当然会把他永远铭记在心。拉法格证实说,“马克思能背诵歌德的许多诗句”[21],他高度地评价了歌德那种“洁白无瑕的风格”,“幻想和心灵的语言”。歌德的诗,是文字的必然装饰品,——他有权与莎士比亚的诗相媲美。在《资本论》里,继莎士比亚之后,引证最多的就是歌德,更确切些说,就是他的《浮士德》。实在令人注目啊!在这部足有700页的篇幅里,歌德的诗,在这里只是由这部不朽的悲剧所代表,——我们同剧中的主人公,时而在浮士德的书房里,时而在奥尔巴赫酒馆,时而在城门之外,时而又在天上相遇。当然喽,《资本论》里,浮士德和梅菲斯托费尔关于人和他在地上的地位,展开一场悲剧性的争论,惊天动地,这也决非是偶然的。
是的,歌德与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并称当之无愧。他是后起的祖国之骄,人民的财富。所以对他的爱,才是那般的狂热和经久,那般的繁复和严苛。对共产主义导师来说,展开一场捍卫伟大预言家精神遗产的激烈斗争,决然是非同小可的。
他们保护着歌德,使他免遭形形色色的推翻者、无情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僧侣主义的谋害,这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写的那些尖刻的题诗看得出来,马克思的诗是对着路德派新教的牧师、反歌德十字军的首领普斯特罗亨而写的。
他们保护着歌德,使他免遭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谋害,它鼓吹超阶级的“全民”理想,以及市侩地把这位伟大古典作家打扮成“理想人”,为此,恩格斯在一篇科学著作中,对格律恩[22]的全部骗术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
他们保护着歌德,当然不是保护歌德作品中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上摇摆不定的东西。恩格斯在下面的一些话里,辩证地表达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痛苦以及马克思对歌德的爱: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23]
马克思所推崇的三位诗人,按我们习惯上的理解,都不是革命家,可他们个个都能成为人类的一面镜子而加以借鉴。此外,他们又把马克思的三个祖国强有力地体现了出来。古希腊罗马——是他精神的摇篮,德国——是他生育的地方,英国——是天才安身立命之地。
[2]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4]“耳聋的上帝”、“富人的国王”、“虚伪的祖国”,源于海涅著名的诗《西里西亚之歌》。
[7]此处形容三位诗人的诗具备“复调音乐”的特点。“复调音乐”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其中若干旋律同时进行而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8]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掌管商业、交通、畜牧、竞技、演说以至欺诈、盗窃。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
[9]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51—152页。
[17]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1卷,第97—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