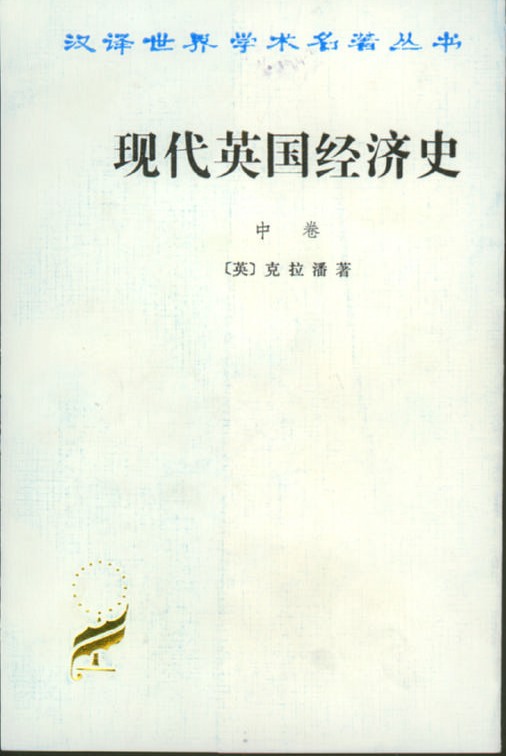
序
本卷所以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相当快地踵随上卷之后出版,我想主要是因为材料不太宜于迅速处理的缘故。材料为量既巨而又残缺不全;其中很多都没有经过精细拣选。其次是由于,愈靠近社会和经济统计数字完备的现代时期,某些部分的记述,就愈难下笔。英国卷入“世界经济”愈深,叙述也就愈不应局限于本岛一隅。艾尔弗雷德·马夏尔常常这样说:在 1870 年以后你就无法编写英国经济史了。他未始不可把日期再提早一些。以统计数字适应文字记述和以英格兰适应世界的这种写法,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就,这是有待读者评断的。然而试图这样去作却着实花费了一番工夫。
材料所以残缺不全,部分原因是维多利亚朝中叶人生活于的确愈来愈舒适而又运行得没有太多摩擦的一个世界中,所以没有指派象维多利亚朝初叶人那样多的调查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专凭赖事实上主要关系于经济和社会病理学的那些日积月累的调查,使我们狃于十九世纪早期的看法而不能自拔。有时我也的确认为如此。但是细心阅读这些报告书,则发现有关正常社会细胞的叙述也几乎同有关病态社会细胞的论列不相上下。例如卡尔·马克思大加利用的少数得自维多利亚朝中叶的较早形式的报告书之一,即有关六十年代童工问题的那一件,就是充满了关于工业组织的附带材料的。六十年代的职工会调查亦复如此。幸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维多利亚朝末叶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抱杞忧,又恢复了对各种情况的调查,而且规模之大,几令人却步。在四、五大本《工商业萧条》之中有追述过去的丰富材料;而在九十年代的那六十七大本《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附有编制完美的索引,裨益学者匪浅——以及在查尔斯·布思的九卷《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之中,则材料更加丰富。
凡官方和其他精确的原始材料缺乏之处,就深深感觉到第一流地方史籍和行业记录的不够充分。我总念念于劳埃德的《刀具业》(1913 年版)、赖特和费尔的《劳埃德咖啡店史》(1928 年版)或艾伦的《伯明翰和黑乡的工业发展》(1929 年版)这类书籍。鉴于自本书上卷出版以来,最后两书和我所利用的包括韦伯夫妇有关济贫法等著述在内的其他很多书籍和论文的问世,可知本卷如欲求精进而再候——我们可否说?——十年出版,将会有多少材料可供汲取。但是我无法再候十年了;不过我相信我所利用的材料是信实可靠的,虽则仍有不详不尽之处。
就本卷而论,我叨惠于艾尔弗雷德·马夏尔的厚赐为独多。在他逝世之前几年,承他将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那套装订成册的《经济学家周刊》委托给我保管,并惠允我直到写完这一段时期之后再移交给马夏尔图书馆。有幸和这段时期的编者华尔特·白哲特漫步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实业界, 而且可以说步随其左右,这的确是一种不平常的权益。比之大多数经济学家、行业史学家或调查委员会的秘书们,他是更加精力充沛,更加渊博的。
为搜求格拉斯哥、利物浦和格里姆兹比方面的材料,承蒙提文斯先生、哈巴克先生和约瑟夫·贝奈特先生惠助,良深铭感。在第 626—627 页上所利用和引证的有关郊区建筑术的材料,则叨惠于莫伯利先生者实多。在英王学院的同事之中,我应该感谢庇古教授,他或惠假书籍,或在那个经济学家的我对于那个历史学家的我的繁重无比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时惠予鼓励—— 这是他所早已忘记了的;感谢约翰·索耳特马希先生惠允从我们的契据之中选取材料供我个人使用;感谢马考莱先生惠允借重于他狩猎方面的回忆和他对于塞提斯的工作的全部知识;并感谢汉密尔顿·麦孔比先生惠为核对化学工业方面的参考书籍。对于最后一位则尤应特致谢忱,因为我深信一个惯于过分烦琐的著者,只能自己去冒错失的风险,而不应该以他的校样去麻烦朋友的。因此,对其他一些段落,以及对这些段落,我就自冒风险了。
我不能因为以《一千零六十六行》(1066 and All That)为题的那部记录的问世,就不感谢我的妻子在索引方面所作的一些极其繁重的工作。英国当代人自会了解如何查阅参考书籍,但是我的这部书果能流传一、二十年,使外籍人士和后进学子有此索引可供查阅,会是不无裨益的。
克拉潘
1932 年 5 月 1 日于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