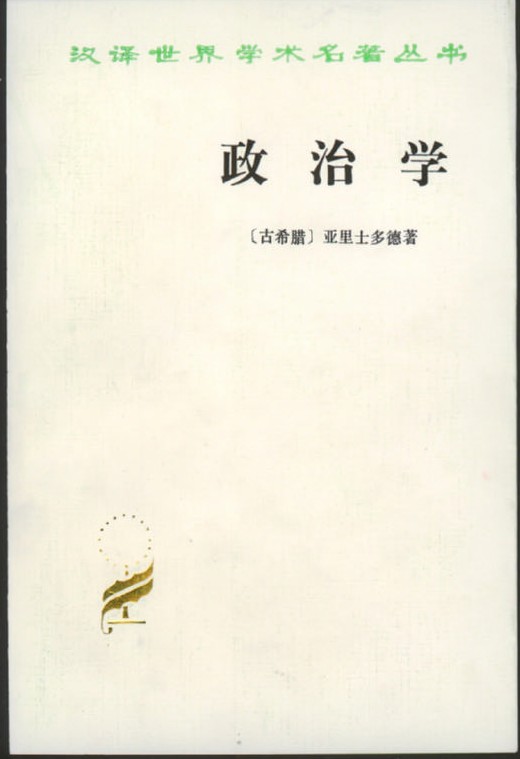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吴恩裕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是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许多学科中,如哲学、伦理、逻辑、心理、物理、生物等等,他都写下了开创的或重要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也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有剥削阶级的政治学,也有被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用剥削阶级的观点创立政治学的体系,亚里土多德实为第一人,他的
《政治学》也是一部首创的著作。在他以前,曾经有过奴隶主阶级的著名政治家,如梭伦、伯利克里,但他们没有留下政治论著。曾经有过片段的政治见解,如辩士派和苏格拉底的某些主张,但那都不成其为政治论著。也曾经有过像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的著作,但那部书与其说是政治论著,倒不如说是杂揉哲学、伦理、教育以及政治的混合著作,不能说是创立了剥削阶级政治学的独立体系。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两书,就其骨架的狭小和内容的单纯来说,也都不能算是建立了这种政治学体系的著作。惟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在下远意义上,的确可以称为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之作。
第一,《政治学》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和原理的著作。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讨论政治学的问题是和伦理学的探究分不开的。例如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把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问题,亦即伦理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的。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把两者截然分开了。他对于伦理问题的探讨,另有一部《伦理学》。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分家,正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主要条件。当然,伦理和政治的彻底分家,还有待于马基雅弗利(N 1ccolo Ma.HIAhhVolli,1469—1527)的《君权论》(1513 年)一书;但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对的分家,却不能不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第二,我们说《政治学》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创始著作,不仅由于它是一部专门讨论国家和法律的政治论著,而且也由于《政治学》一书的体系和内容与西方责产阶级的政治学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学者对《政治学》一书的考据所得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就结构和内容而言,有人认为《政治学》中各卷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讨论理想中的国家的,第二、三、七、八各卷属之。第二组是讨论实际政制的,第四、五、六等卷属之。余下的一卷是结论。但也有人说,《政治学》是由三种单独的论文组合而成的。第一种论家庭,如第一卷。第二种论前人理想国的见解以及当代最完备的宪法, 如第二卷。第三种论国家、公民及宪法的分类,如第七、八两卷。这两种考据结果似乎是不同的。可是,根据《政治学》一书的实际内容而言,它基本上包括两种问题的讨论:(一)关于政治理论的讨论;(二)关于现实政(HJ。 Laski,1893—1950)的《政治典范》,在美国流行的教科书如迦纳(James Wilford Garnor,1871—1938)的《政治科学与政府》,在体系上,都是先泛论国家的性质,然后再讲政治制度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它们都没有摆脱亚里七多德《政治学》的影响。
第三,除了以上两点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说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一书确实是剥削阶级政治学的一部最早的著作。这个理由就是, 尽管《政治学》一书中所贯彻的观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却是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本质上有相通之处的。这就是说、尽管奴隶主的犹市国家不同于封建领主的封建国家、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尽管后二者都各有其独特的性质和经验,但是,它们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说,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压迫工具;从而,研究这些压迫工具,在理论上便有相通之处,在实际上也有共同之点。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这部《政治学》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在本文以下各节,我们第一,耍指出《政治学》一书中所包括的奴隶主阶级的观点。第二,耍指出这一观点在哪些方面的应用是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通的——亦即后来被封建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是“政治学”中的永久不变真理。第三,要指出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实际政治的态度和主张是什么。
二
亚里土多德生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怕罗奔尼撒战后,雅典社会各阶级如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受到战争的很大影响,农民更遭到严重的损害。由于土地集中于大奴隶主千里,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和高利贷者的盘剥,许多农民无地可耕,只好跑进城市里去做自由贫民。战争使雅典的国库枯竭,以致不能执行旧有的对城市贫民的配给和援助政策。雅典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于尖锐化。
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雅典奴隶主国家发生严重的动荡不安,不但在雅典,而且在每个希腊城市国家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基本矛盾之外,都有富有奴隶主阶层同自由贫民之间的激烈斗争。对于这一情况,柏拉图曾经有过希腊的每一城市国家都已分裂成为“富人之国”和“穷人之国”的慨叹。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公元前 399 年,斯已达发生了基
拉东自由贫民的起义。公元前 392 年发生了科林斯自由民下层反对寡头势力
的流血斗争。在亚里士多德的幼年,公元前 373 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棍棒党起义,他们杀了富有奴隶主,浚收并分配了他们的财产。自由贫民与富有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希腊城市国家末期的主要矛盾。
至于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奴隶,他们当然是要反抗奴隶制度的。他们虽然没有溜下多少文字材料,但是希腊历史各个时期的奴隶起义,便是最好的说明。就思想史而言,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人提出反对奴隶主国家和法律的思想,在希腊戏剧家所写的剧本中,也有这种思想的反映。其后,虽然由于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史的资料流传下来,但是,他们反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国家的思想和感情,却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的行动和思想同奴隶主阶级的行动和思想构成了奴隶制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
目击希腊、特别是当时作为希腊文化重心的雅典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从中等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力量的办法来平衡富有者和贪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奴隶主国家不至崩溃。
亚里士多德生于斯达奇拉城。他少年去雅典柏拉图的书院读书,受柏拉
图的影响颇大;但后来终于摆脱了他的影响,而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公元前 342 年,他做了马其顿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亚历山大公元前 336 年即位,亚里士多德便回到雅典郊外的里栖阿姆(Lycoum)设立书院,招收生徒,从事讲学,直到公元前 322 年死时为止。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摇摆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他“对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并无怀疑”,所以接近唯物论。但他又认为:万物的基础及其内在的本质却是形式,物质只是它们的第二个基础和本质。他主张形式先于物质。这便又是唯心论的主张了。在认识论上,他也动■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方法之间,可是他却“研究过最重要的辩证思维的形式”,而与黑格尔同为思想史上曾经对于辩证法或多或少加以精确研究的两个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二元和折衷的思想和态度,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反映。
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相同,他们却都是奴隶主国家的忠实拥护者。然而,就是在柏拉图的时候, 也已经有了某些奴隶主阶层分子,鉴于城市国家中不断的“党争”,根本厌倦了城市国家的生活,怀疑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须参加国家生活”的看法,而认为:在道德上,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国家的生活可以与此无关。苏格拉底的学生安蒂叙尼(Antistlienes)的制欲主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这种“隐逸”或从国家中“引退”的思想,大肆攻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曾经斥责那种把生活的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上去,是“猪的国家”而不是人的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说过:一个人若能离开国家而生存,他不是个野兽,便是一个神。这师徒两人的逻辑是:不加入城市国家就不可能过人的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坚决拥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们之有这种想法是不奇怪的,因为维护奴隶制度首先必须维持奴隶主的国家政权。
远在公元前五世纪,欧里庇特(EurideS)的剧本中就有反对奴隶制度的明显主张。
“只有一件东西给奴隶带来耻辱, 那就是‘奴隶’这个名字;
在所有其他方面,
奴隶并不劣于自由人,
所以他也有个公正的灵魂。”
这就是说,从“自然”出发,奴隶制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奴隶和自由民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从为奴隶,完全是“人为的”,那是社会制度使然。可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奴隶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奴隶生来就比常入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 他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他们是工具, 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是活的工具,而不是“人”。如果说上引这类词句只是些反对奴隶制的标语口号,那么,柏拉图对话集中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里 所说下面的话,不管原来是为了证明什么结论,至少也可以作为“奴隶是强力造成的结果”的论证:
“⋯⋯假如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然力量,⋯⋯把我们成文的法令、欺骗和鬼话,以及违反自然的法律,都一概摒弃,并且置诸脚下,那么,这个人
不但不能做我们的奴隶,而且还要超乎我们之上,做我们的主人。”
可是,对于这种分明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演变而产生的、用国家暴力镇压来维持的奴隶制度,亚里上多德却硬耍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制度。可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偏见是极深的。在这种偏见之下,他便把国家视为公民的联合团体,而他所谓“公民”,则是指既有治人的能力也能被治的人们。这样,在公民中不但排除了和他们同是圆颅方趾而只是不被当做“人”看待的奴隶,也排除了劳动阶层: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人民过于依赖他人的命令,而没有统治的能力, 所以不适宜于享有公民的特权。他所谓“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中的“人”,也不过只是奴隶主富有阶层的代称而已。亚里士多德这种看法, 显然是对于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的一种辩护。因为,事实上,在雅典这个“最民主的”希腊城市国家中,能够参加所谓“直接民主政治”活动的, 也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阶层而已;至于贫苦的自由民,是没有机会参加那种活动的。
正是在对于公民持这样一种看法下,正是把国家视为这样一些公民的联合团体,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对国家性质、目的和起源的学说。
三
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政治学》开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上节所讲公民的身分和政治生活的成员和内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阶级暴力,它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压迫其他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就希腊的城市国家说,很明显,它是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的。在这些意义上,政治学被他认为是最高的科学。
这一说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学说。固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但他的手法却是先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然后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而个人觉得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可是,亚里士多德却把国家同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并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说什么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它的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找出理由,说明国家是必要的、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后绝大部分的剥削阶级思想家袭用亚里士多德否认国家阶级本质的办法。西塞罗
(Cicero,公元前 106—43)说国家是“人民的事务”,阿奎那(A QUnas, 1227—1274)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这些固然都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BOdin,1530— 1596)认为主权是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划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标准的看法,也显然可以从中考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和基本概念。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Locka,1632—1704)、卢梭(Boussoan,1712—1778)等等,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边沁(Bentbam,1748—1832)、孔德(Comte,1798— 1857)等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学家如狄骇(Dngui,1859—1928)、凯尔森(Kelsen,1881— )等等,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论据来掩盖国家的阶级
本质,他们都是采取先把国家和社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分开,然后再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一办法的。当然,采取柏拉图那种把国家同社会混为一谈而后再说明国家权力的必耍性的办法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个办法在社会愈益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愈益趋于激烈之后,便愈发不能欺骗人民了。
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他们一套手段和“理论”;但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国家理论, 根本上是由于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使然;但也正由于他坚持奴隶主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他也就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一方面认为国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这个“历史的”过程发展的结果,另方面却又用“人的本性”(man’S naure)这一概念来阐释国家之所以为“最高的”团体的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医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学方面知识的影响。他对于“自然”(naure)是采取生物的观点的解释。这一生物的自然观、本然观或本性观,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而终于认为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了它们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如一根树苗虽然具有其所以为树的本性,但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动物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说: “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就个人论,他不是“自足的”,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最高的,使“快乐而光荣”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则是国家的生活。从个人到国家被他看成是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由根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人性论虽然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新兴的“中等阶级”所制造的理论, 但它的萌芽却是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找出来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被剥削者的基调,总归是一致的。在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议论中之所谓“人的本性”,显然只是奴隶主统治阶层的阶级本性。只有他们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并且要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而奴隶则适得其反地要推翻这种统治。希腊的奴隶主不把奴隶当做“人”,然而奴隶毕竟都是人,他们有的是一些陷于深重的债务不能白拔的 1 穷人,有的是一些军事上战败的俘虏,也有的是为了其他原因被插上标志在奴隶市场上出卖的人。而且,自由贫民到了无以维生的境况的时候,也并不那么爱那个城市国家。由此可见,不但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性,即使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 也反映着对同一政权的不同态度。在希腊的奴隶起义中有自由贫民参加,贫民起义中有奴隶参加,这不正好表明他们对奴隶主政权的一致态度么?因此,所谓国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只能意味着国家是奴隶主的阶级性的要求的充分实现。“人”同国家的关系显然是和生物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不同的。这种用生物成长的过程来和从个人到国家的发展相比拟,显然是不伦的比拟。尽管亚里士多德这种说法后来仍被封建时期以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某些剥削阶级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它的掩盖阶级的、反科学性的实质,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有人甚至说,这恰恰足以证明他的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思想。但这一说法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柏拉图是以法治为“第二等好”的统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的或最好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以不同。因此,我们把
他对于法律的看法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
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得很干脆: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治中的“人”, 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未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奴隶是不在话下的),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法律上的权利; 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统治者也不敢胡做非为,破坏法纪。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的看法,同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一样,都是根本否认阶级性的。当我们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时,我们认为那“意志” 之中当然有这个阶级的“智慧”和“感情”在内。难道在镇压奴隶的希腊城市国家的法律中,没有奴隶主阶级的“感情”和“意志”么?难道在寡头制度的立法中,没有寡头势力力求压制民主势力的“感情”和“意志”么?显然是有的。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曾经研究过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在今天残存的《雅典政制》一书中,他也记述过许多富人当政立法,穷人起而反对的事实:难道在那当政的富人所立的法中就没有他们压迫和盘剥穷人的“感情”和“意志”在内了么?回答也只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的看法,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掩盖法律的阶级实质的。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可以看出希腊奴隶主阶级对于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一般看法——那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统治永远是个大前提。
四
然而,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究竟代表哪个阶层的耍求呢?这就必须考查一下他对实际政治的态度和主张了。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一方面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加深,另方面富有奴隶主和自由贫民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本文作者按:当做‘阶层’理解)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居于中间”。第一个阶层, 他又名之为寡头势力,第三个阶层,他名之为民主势力。两者都力求攫得政权,以便实行代表自己利益的寡头制或民主制。斗争不已,遂使当时的希腊奴隶主国家动荡不安。亚里士多德担心奴隶主国家的分崩离析,逐苦心孤诣地寻求稳定奴隶主阶级江山的途径。
作为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所开出的挽救城市国家危机的药方,是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所开的药方不同的。柏拉图代表富有奴隶主阶层,借口必要的社会分工,来严格地划分阶级,企图固定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和职事,从而巩固奴隶主上层的阶级统治。他不但仇视民主势力,也无视中等阶层的地位,他的“哲学王”一方面固然是知识贵族,另方面也是奴隶主上层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则不但认为富有阶层“狂暴”“暴戾”,并且也认为贫穷阶层“下贱”“狡诈”。“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惟有中等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他们不像贫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也不像富有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因此, 中等阶层“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
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穷人凯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亚里士多德既然在伦理学方面崇尚中庸的美德,那么,在政治学方面,他也认为“中庸适度”是“最好的”;而中等阶层在城市国家中恰恰是这个“中庸”的化身。“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惟其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便把巩固希腊城市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中等阶层身上。
究竟怎样来巩固或“稳定”呢?关键在于财产和人数的比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中等阶层的人数比较多,而中等阶层就是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层就能衡平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争之祸”——亦即当时希腊奴隶主国家中的富人和穷人不断斗争之祸。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 也没有必要害怕后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反对中等阶层:他们是永远“彼此互相不信任”的,不会合作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后认为:只有中等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也“只有在中等阶级[阶层] 较其他阶级[ 阶层] 之一或较两者都占上风的地方,政府才能够稳定”,所以“最好的立法者都是中等阶级[ 阶层] 的人⋯⋯例如棱全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了棱仑,并不是偶然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梭仑这位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奴隶主国家的立法者,是如何的赞扬与同情。他说:梭仑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仑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这种主张恰恰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相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温和民主制”的主张,也是他对当时奴隶主国家所持的态度。这是一种什么主张和态度呢?很明显, 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和态度。他看到了城市国家的“党争”的核心问题是财产不均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根本变更财产制度,而是企图用局部改变中等阶层的人数和地位,来“改变”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矛盾形势,从而“稳定”奴隶主国家的动乱不安局面。然而,在我们看来,他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希腊的中等阶层,正如小资产阶级之在近代一样,他们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希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等阶层或者上升为富有阶层,或者下降为贫穷阶层。那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个不稳定的阶层。用一个经济地位不稳定的阶层来“稳定”由于另外两个阶层的矛盾和斗争而致不稳定的国家政权,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奴隶主阶级的爱智者(即哲学家)的智慧毕竟是受他的阶级立场所局限的,他看不到这点。相反,由于阶级感情的驱使,他还在《政治学》中费了一些篇幅提出预防革命的办法。他所探索的那些革命的原因, 都是为他的预防革命的感情或目的服务的。一个具有类似改良主义思想的思想家之反对革命,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希腊奴隶主国家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亚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制企图在保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在根本保存大富极贫的前提下,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势力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终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假使没有亚历山大所造成的军帝国的“希腊化”局面而使希腊各城市国家自然发展下去,它们的命运也必然是日趋分崩离析而濒于危亡。因为除了奴隶的起义之外,自由贫民同 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也已激烈到了极点。柏
拉图早已经说过:“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造反。”由于“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统治阶级由军事和政治胜利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才使奴隶制国家在另外一种形式和规模下又继续了下去。
亚历山大成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死。然而我们今天却丝毫看不出:他这位“高足”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当时所造成的世界的新局面对他有任何影响。亚历山大揉合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以非希腊人为“野蛮人”;亚历山大把城市国家沦为意义大为降低的市府或省区, 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认为它是“良善而自足的生活”的标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已落在政治现实的后面了;它们是属于一个结束的时代,一个用城市国家的方式来统治的时代的理论的。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他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人。
1964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