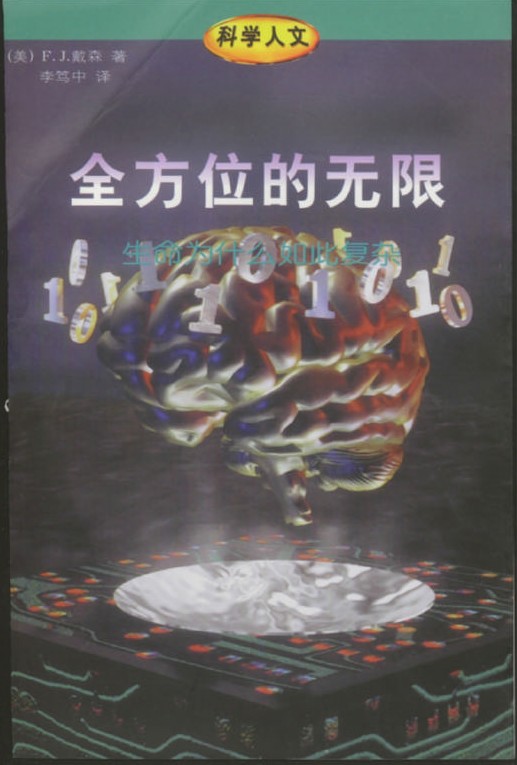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系黄舒兰。
她怀看对海外长孙的刻骨思念,于一九六一年含泪长眠。她终生谦恭仁爱,
默默的忍受着命运的驱使。
大灭绝──找一个消失的年代
第一章 学海疑云
我在八年抗战的烟硝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其对,我正客居于陪都重庆。各种伦理教育纷至沓来,矛盾百出,令人无所适从。家里是慈母的训诲;她崇尚孔孟之道,劝我一心向善,待人仁义为先,同时夹杂着道家听天由命、克己为人的思想。学校里是师长的教导;他们的教育中掺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每日清晨,学生都要排队作操半小时锻炼身体;余下的时间是聆听师训, 告诫我们要刻苦磨炼意志,以便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强者。理由很简单,现实世界,到处是优胜劣汰。忍受不能赋予我们力量(尽管母亲倡导这种人生哲学),只有仇恨才能使我们由弱变强。
几乎与此同时,在战线的另一方,德国青年正在接受戈培尔的说教,并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汲取纳粹思想。按照这些教师的逻辑,芸芸众生中只能有一方获胜。岁月如梭,物是人非。如今我们都和平共处,彼此成为同事、邻居或朋友,显然与戈培尔的预言背道而驰。当然,我的母亲地下有知, 是会感到欣慰的。
尽管我们有幸成为这场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但却又都是一种冷酷社会思潮的牺牲品。这种思潮断言: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竞争,都属于生命的自然现象;优胜者压迫弱小者是天经地义的。一百多年来,这种思潮被奉为科学的自然规律,风靡全球。它就是主要由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达尔文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天择思想, 就是这种进化观的完整表述。
时光荏苒。从抗战到现在,已经整整 40 年过去了。根据战时和战后发生的一切,展望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变故,我不禁要问,这场残酷的斗争究竟证明了什么?生者、死者,究竟谁是适者呢?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以为应当三思,冷静的思考这种为害不浅的观念究竟有多少科学可信度。
恐龙化石出土
达尔文是一位研究生命史的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球上的生命史,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球上现存的物种虽然数以百万计,但是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却几乎都灭绝了。因为在五亿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某一时代的物种总数变化不大,但物种的平均寿命是短暂的,就像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生命十分短暂一样。现在还活着的种,大约只占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生物的百分之一。
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任何一种生物演化理论,不仅要解释物种的新生,而且必须解释物种的灭亡。对达尔文来说,生物灭绝的机制与生命产生的机制毫无二致。每种生物个体都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其他生物,而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如此难以胜数的生物个体中,自然界进行着独具
创意的选择,只有那些机能的特征最能适应其生活方式的种属,才能幸存下来并不断繁衍,将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反之,不适应者只有灭亡一途,其弱点亦将从种群中消失。当某种变化中的种群因为某种原因与主体的演化趋势隔绝,而无缘发生混种时,就会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种。尔后遇到有亲缘关系的种属时,其中的一种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无情的扑灭竞争对手。达尔文如此解释他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他写道:
我想,生物界将无可避免的遵循这一规律: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物种通过天择应运而生;而另一些物种则日趋减少,乃至灭绝。起源相近的生命形式,同一种群的各种变体, 同一属或相关属的物种,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结构、素质和习性,通常会陷入最激烈的竞争之中。结果造成每一个变种在演化进程中,势必对最接近的宗族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求置之于死地。
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恐龙和其他古代生物,但生物灭绝事件听来仍相
当古怪,在达尔文时代就更不用说了。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认识了化石, 尤其是介壳化石;虽然与现代种属迥然不同,但它们也可能仅仅代表了生物从一个种属向另一个种属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早期形态。从这种考虑出发,把一种早期生命形态的消失称为灭绝显然是欠妥的。就像人类从呱呱坠地成长为伟男子的过程中,把孩提时代称为生命形式的灭绝同属谬论一样。但种属灭亡是的确有的,恐龙灭种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爬虫骨骼发现于 1770 年,大约比达·尔文的生年还
早 40 年。这种爬虫与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毫无相似之处;下颚骨化石长达四英尺(一又三分之一公尺),牙齿锋利犹如短剑,最先是在荷兰的马斯特里奇(Maas-tricht)村圣彼得山上一个采石场的白垩层中发现的。这一发现使人大吃一惊,于是村民将一对父子解剖学家请去鉴定。鉴于骨骼奇大,又恰恰夹在两个富含海相化石的地层之间,父亲便声称这是一条古鲸的化石。但是儿子却另有高见。可能是因为研习解剖学更精或观察事物更为敏锐之故吧,他认为这种生物更像蜥蜴。但是,有谁见过如此庞大的蜥蜴,又有哪一种蜥蜴能在大海中途游呢?似乎只有把这种怪兽解释成圣经所载洪水事件之前的生物,而且可能就是那次洪水的祭品。
发现怪兽化石的采石场之上是一片牧场,场主是一位教士。他运用本身的封建权力攫取了这一发现,把遗骨安放在乡间别墅的一个玻璃神龛里。于是,发现洪荒巨龙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名噪一时的解剖学家居维叶
(Georges Cuvier)的耳中。当时,拿破仑一世是居维叶的积极支持者, 曾助他从事化石采集。拿破仑获悉怪兽化石的新闻后,立即命令他的将军率师“解放”荷兰,以便将那块宝贵的化石完整无损的抢回法国。那年是 1795 年。这支队伍长驱直入,直达马斯特里奇村,占领了那间乡间别墅,但玻璃神龛里竟然空空如也。那块化石已经不翼而飞了。
将军灵机一动,决定悬赏追寻,赏格是葡萄美酒 600 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批长于打家劫舍的大兵终于得到了这笔重赏,于是这一战利品也
就安全的运到巴黎市居维叶的办公桌上。
其时,居维叶风华正茂,年仅 26 岁,刚刚完成乳状牙象(mastodon 另一译名为乳齿象)骨的研究。他认为,乳状牙象并非现代象的祖先,而是一种在历史上早已消失、而且没有后代的古象。他开始竭力说服他的同代人, 要他们相信历史上确曾存在过这种生物灭绝现象,而马斯特里奇巨兽就是他所需要的证据。虽然这种名叫沧龙(Mosasaurus)的动物看上去与热带的陆生动物极为相似,而且也曾被称作蜥蜴,其实却是一种比普通蜥蜴大许多倍的海相爬虫类。
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平息之后不久,又于 1822 年首次发现恐龙化石。
当时达尔文还只有 13 岁。这批恐龙化石只不过是一堆碎片,其中包括一块股骨和一些硕大的牙齿,由英国南部的化石采集家孟特尔夫人( Mrs. Gideon Man-tell)挖采出来。她认为这些化石是一种爬虫的遗骸,而当时人们熟悉的爬虫都是牙齿锐利的食肉动物。然而孟特尔夫人发现的牙齿冠部已经磨平,应属食草动物。
人们又去请教居维叶,居维叶证实这些确是食草爬虫的牙齿。后来,孟特尔先生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汉特林博物馆 Hunterian)中见到了鬣蜥骨骸。除了大小的差异之外,那枚恐龙牙齿与鬣蜥的极为相似,因此他将它定名为禽龙(Lguanodon,鬣蜥牙),并于 1825 年正式公布了这一发现及其新名称。
以活鬣蜥的牙齿大小为标尺,牛津大学教授欧文(Richard Owen)作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推论:禽龙的身躯应在 30 至 60 公尺之间,算来竟有半
个足球场那么长。于是,盂特尔先生和其他业余研究家又继续发掘,在 15 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现了肋骨、脊椎骨和其他许多骨头。这些骨头的大小迫使欧文不得不修改原来的推论,于是禽龙的身长降到了七公尺。化石还显示这种古龙要比现代的巨蜥大得多,也重得多。其胸骨的结构与鳄鱼相似,心脏有四个心室,比其他爬虫类只有三个心室的心脏进步。欧文指出,该动物的心脏和循环系统已与温血脊椎动物相差不远了。
欧文把这种动物命名为恐龙(Dinosauria),意即“可怕的巨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为此特地找到一位野生动物雕塑家,要他根据欧文的描述为 1851 年的博览会雕塑一尊巨蜥的塑像。于是禽龙就以一种硕大而笨重的四足兽形象,虎视眈眈的呈现在来访的权贵面前,其中包括女王和她的丈夫。
当时,美国未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海顿(FerdinandHayden),正在蒙大拿州裘迪斯(Judith)河附近的西部荒原采集恐龙牙齿。标本送到费城的美国自然科学院,由院长雷迪(Joseph Leidy)加以研究,发现这些牙齿属于另外的恐龙属。雷迪将其中的一种食草恐龙命名为 Trachodon(意谓粗糙的牙齿),而将另一种食肉恐龙命名为 Deinodon(意谓吓人的牙齿)。
事后方知,这些牙齿其实只是一些不足挂齿的诱饵,真正的室藏还埋在
地下。不久,雷迪就在新泽西州的哈东菲尔德(HaddOnfield)发现了一副几乎完整无缺的恐龙骨骼,并命名为鸭嘴龙(Hadrosaurus)。所发现的牙齿、下颚骨、脊椎骨,以及肱骨、桡骨和四肢的尺骨,都属同一个体。将鸭嘴龙的牙齿与禽龙的牙齿比较之后发现,尽管前者的骨骼与雕塑家根据欧文的描述重塑的形象几无相近之处,但这二种绝种恐龙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鸭嘴龙和禽龙的前后肢相差极为悬殊。因此雷迪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四足兽,而是一种后肢能够站立,可以像袋鼠那样跳跃行走的动物。
奇形怪状的兽骨
恐龙的挖掘工作终于风靡一时。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由商界巨子组织的采集队相互争夺,日趋激烈,力求要满足后台老板的好奇心,于是出现了一批扑朔迷离的兽骨。他们把这些真假莫辨的战利品集中起来,进贡给统治者;然后在皇家或国立博物馆中陈列,博取目瞪口呆群众的赞誉。
有些骨架的确大得惊人。雷龙(Brontosaurus)和腕龙(Brachiosaurus) 体重达 55 吨,等于八只大象加起来那么重。有人认为,这样的庞然大物无法在陆地上生存,于是设想那是一些在沼泽中生活的动物。它们用细长的脖子采食水草,或者浸泡在水中并以头顶上的鼻孔呼吸。在食肉动物中,最大的要数霸王龙(Tyrannosaurus rex)。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动物,牙齿与鹤嘴锄一般大。将它的骨架树立起来,沉重的尾巴拖在地上,常人身高仅及其膝部。观者无不为之瞠目结舌。
有时恐龙具有独特的躯体外部饰物或武器。有的身披重甲;角龙的脖子上长满了大片的饰骨;剑龙的背脊和尾部长满钉刺;鸭嘴龙有奇怪的头冠; 禽龙长着特殊的指甲,可以用来对付刀枪不入的食肉动物,挖出它们的眼睛。
在化石争夺战中, 人们又发现了一种牙齿很小的动物。翅膀像爪子,有着长长的羽毛,外形很像希腊神话中的格里芬(一种鹫头狮身的怪兽)。由于被认为是最原始的鸟类,因此称为始祖鸟。人们结合沉积物的特征研究生物习性,发现爬虫类——并非单指恐龙——真像神话故事中的动物一样奇妙。薄片龙(ELasmOsaurus)是一种海龙。正是对这种怪物的遐想,才激发了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的传说。翼龙则是一种长着翅膀的爬虫类,有的只有乌鸦般大小,甚至还要小一些;也有的像苍鹰那么大。有一种可以飞在海上的翼龙,其翅膀竟长达 15 公尺,可能已达飞行动物的最大极限。显然,翼龙的翅膀太重也太脆弱,并不宜于飞行。因此有人认为翼龙是一种滑行动物,只能以树顶或悬崖为中介进行滑翔。
生存竞争
按照达尔文的意见,这些横行在 6500 万年以前的怪兽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失却了生存竞争的能力。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就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作一个“由成万个锲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打着那个”。每一个楔子好比一个生物种或变种, 而每一次敲击就是天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挤出一个不可。因此,一个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想必会排斥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二次大战时,瑞士边界难民云集,人满为患,瑞士人封闭边界的藉口是“船已满载”。从达尔文的观念看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也十分类似。
达尔文的种数空间有限论,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空间有限论。在他的自传里,达尔文写道:
1838 年 10 月,正是我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后的第十五个月。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的脑海中已经孕育了生存斗争的思想。根据对动植物生活习性长期不断的观察,我发现这种斗争无处不在。马尔萨斯的著作立即吸引了我。在有限的空间里,只有适者才得以存续,而不适者势必遭到毁灭。结果形成新种。于是,我终于找到了一种继续工作的理论基础。
20 年后,达尔文才出版这一思想。他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一位名叫
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年轻人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达尔文“出于好奇”而拜读马尔萨斯的著作 20 年之后,在地球的另一方,靠近新几内亚的一个岛屿上,华莱士也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 得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想法:
其时(1858 年 2 月),我身患疟疾,蜗居在摩鹿加(MoLuccas)岛上的特尔纳特村(Ternate),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忍受着忽冷忽热的煎熬。病中浮想连篇,物种起源问题总是萦回脑际。一日,忽又想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十年前我曾读过此书)及其所谓的“有效控制机制”——战争、疾病、饥荒、突发事故等等,这些机制可以控制野蛮民族的人口至近乎稳定。于是联想到,这种控制当然也适用于动物,使其数量不致无限增长。但对这些控制作用如何影响物种,我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看法。忽然间,适者生存的思想闪过我的脑海。总体而言,这些控制作用将使较劣者消亡。我想到,动植物的每个新世代都存在这种变化, 而与此同时,气候、食物和天敌的变化也在不断进行,物种的变化过程终于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于是,我在发病的两小时内悟出了这一理论的要点。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首版印行于 1798 年。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二
百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许多社会学科的必读课程。中国的经历可以用来说明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在近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中,中国的人口一直保持稳定。1949 年内忧外患宣告结束之后的三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从五亿增到了十亿。按照这一增长速率,中国的人口到 2110 年将达到 20 亿,
2140 年达到 40 亿,2410 年达到 1 兆。到那时,中国人就真的身无立锥之地了。然而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这种毛骨惊然的人口预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可以控制人口不致连续增长。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公开出版之后,批评之声蜂起。但是没有人针对他的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的信念表示意见。批评者攻击的是,它触犯了普通的遗传理论:按照遗传理论,同一谱系中分属不同分枝的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以及一个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如果把生命树的完整面貌绘制成图,我们就会看到,树的根部只不过是一个单独的生命形态,其他都是它的后代。至于生命形态不断分枝成为新生命的机制,对于那些工业革命时期充满活力的实行家而言,似乎昭然若揭。
达尔文思想被滥用
适者生存的理论立即被奉为自然规律,因为这是一种为资本家的残酷竞争辩护的理论。卡内基(AndrewCarnegie)写道:“无论竞争是否已经开始, 竞争的法则业已建立;谁也无法回避,也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其他法则。尽管这一法则对某些个人而言,有时是残忍的,但对种族而言却最好不过。因为它能保证适者有生存的机会。”约翰·D.洛克斐勒洋洋得意的声称:“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
对于这种新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热情,并不仅限于资本家。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菲立(Enrico Ferri)就利用同一法则转而反对资本主义。他指出, 在阶级社会这种非自然条件下,自然选择是不起作用的。只有纠正了社会财富和特权的不平等现象之后,适者生存的原则才会运行。
当政治家为其或左或右的目的解释自然选择的时候,种族主义者并没有袖手旁观。达尔文原著的副标题“生存竞争中种族的保存”,受到了种族主义者的热烈欢迎。达尔文甚至作了这样的解释:“人种之间也有差异,就像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一样。”正因为如此,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二十年后,才会有一位名叫马歇尔(ALfedMarshall)的英国评论家,恬不知耻的说出了他的一些同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写道:
毫无疑问,英国种族的扩张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英国的下层阶级迅速增长,超过道德和素质都较优越的阶级,那么,不仅英格兰本土的人口素质将遭到破坏,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后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聪明。再者,如果英国人口的增长赶不上中国人,那个无精打采的种族将会蹂躏地球的许多地方,而本来应当是朝气蓬勃的英国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
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乃是一丘之貉。加尔顿(FrancisGalton)创立一个
应用达尔文主义的学派,声称要用“遗传理论、变异理论和自然选择原理” 改善人种的适应能力。事实证明,优生学与灭种屠杀相去不远。
就历史渊源而论,纳粹提倡的种族灭绝可以追溯到哈克尔( Ernst Haeckel)。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人, 竭力为德国的种族主义寻找科学依据。哈克尔最著名的主张就是:个体发生
学再演了系统发生学。他以为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个体发生学,即动物个体从胚胎发育为成年个体的过程,重演了系统发生学,亦即物种从比较原始的形式发育为较高级形式的过程。例如,婴儿的鼻子扁平,通体无毛, 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原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低级”的蒙古(亚洲)人种。而一个高加索种(白种)幼儿的成长,重演了最终成为典型欧洲高级种族的演化过程。哈克尔主义者认为低能儿童染患唐氏症候群的特征, 也代表了一种退化到更为原始演化阶段的现象,因此他们称之为“蒙古症”。过去的生物系学生都在课堂上学过他这一套理论。
哈克尔对所谓“野蛮人”也不乏讥评。他坚持,野蛮人的头骨与尼安德达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极为相似,“像歌德、康德、拉马克或达尔文这类人与野蛮人在智力上的差别,远大子野蛮人与类人猿的差别”。而犹太人,尤其是俄国的犹太人,属于“肮脏而笨拙的”人种,哈克尔认为简直不应列入人类。
哈克尔坚信种族主义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一元论哲学思想。一元论的前提是所谓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夸言这一前提已由他们与劣等民族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所证实。希特勒拣起一元论的衣钵,不遗余力的推行消灭那些“劣等民族”的策略。
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受的一元论教育,比起纳粹德国或今日西方世界的新法西斯分子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诚然,达尔文不应为那些用他的名义所犯下的历史罪恶负责。用萧伯纳的俏皮话来说,达尔文不过是“巧遇别有用心者”而已。达尔文在临终前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被人滥用了。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达尔文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曾经语带幽默地说:“我偶尔在曼彻斯特的报纸上读到一篇讽刺短文,文中说我已经证明强权即公理。因此,拿破仑是公理,骗子也是公理。”
科学的本质
尽管如此,每一个人、每一个科学家还是应当问一句:“适者生存说” 是否真是一种自然法则?或者进而问一句:这究竟能否称得上科学?
公认检验思想究竟是科学或者纯属空想的办法,就是科学理论必须能接受反证。在一般情况下,应能设计出一种实验、研究计划或观察方案。如果实验或观察结果与某一理论的预测不一致,那么这种理论就应当是错误的。 1982 年,阿肯色州的一次庭讯中,曾经成功地应用过这种检验方法。法
官奥佛顿(William Overton)最后裁决,“原创论”(creation science)是伪科学。这场官司是 1981 年,阿肯色州实施“公平待遇法案”,允许学校教授物种起源的原创理论,教学时数与达尔文主义相等;如此持续了一年有余。原创论教导学生:“圣经是上帝圣言的纪录。我们坚信圣经的字里行
间都透着上帝的意志,因此原稿所有的结论,无论从历史的或科学的角度来说都是正确的。对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而言,这意味着圣经创世纪对于物种起源的解释,是一种对简单历史真理实事求是的陈述。”
根据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向法庭起诉。奥佛顿法官必须判定原创论是否科学,抑或只是一种宗教。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原创论的形象遭到了辩护人的糟蹋。一位支持者振振有辞地申言:“谁也无法设计一种科学实验来描述创生过程,甚至无法断言这一过程是否能够发生。”另一位支持者更是妙不可言,声称:“我们谁也无法通过科学研究发现造物主创造生命的任何过程。”那是因为,另一位卫道者补充道,”当代宇宙中并不存在造物主的创生作用。”
原创论者声言无法证明他们的理论不是假的,恰恰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奥佛顿法官除了宣布原创论并非科学之外,别无选择。但是那一次裁决中,并未提出达尔文的天择理论是否为科学的问题。能否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呢?
科学哲学家波琅(Karl Popper)的检验法驳倒了原创论,但他却不认为适用于进化论。他指出,达尔文主义是解释一种历史过程——地球生命史
——的尝试。因为历史是无法重演的(例如,我们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来了解罗马王朝垮台的理论原因),所以波珀觉得,试图判别历史真伪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一种判断或信念而已。
但是,确实可以也已经有人用一些检验方法来判定达尔文理论可能有误。其中成功的检验方法是共同祖先假说。
对一种理论最强有力的检验是它的预见性。波珀坚持,一种理论如果只能解释已知的事实,那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而已。波珀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科学呢?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一种能够预测尚未观察到现象的理论也是科学。这样的科学理论可以反证。如果预测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结果与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那么这种理论的错误也可以改正。反之,证实预言的新发现若是持续增加,这一理论也就愈益逼近真理。
共同祖先
从这一个看法,共同祖先现象是科学理论。达尔文设想,人类和猿猴是由一个共司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观点曾使他的许多同代人怒不可遏。当达尔文于 1833 年首次草草写下他的遗传思想时,还没有发现任何与智人
(Homosapiens,即现代人)不同的骨骼。因此他的理论即使不致使人膛目结舌,至少也像神话故事一样离奇。达尔文预言,如果发现此类化石,它们一定会介于猿猴和人类之间。第一个“遗失的环节”发现于达尔文的理论正式发表前两年,即 1857 年。新发现的智人亚种尼安德特人看上去确实有点
像猿猴。当其头骨和部分骨胳首次在波昂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展出时,有人怀疑并不属于真正的人类,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地质学家莱伊尔(CharlesLyell)发现,“新观察到的猿人骨骼与正常标准人类结构的差别,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或随机的畸形。如果变异法则正合乎进化论者(如达尔文)的要求,那么这种差别是意料中事。”
如果把“实验”一词定义为检验某种假说的过程,那么为了验证某种预测而进行的项目或探索就是一种实验。从发现尼安德特人至今,在欧、美、亚各洲都作了许多对人类和前人类化石的研究,其结果都相当引人注意。目前最原始的人科化石“露西”(Lucy)的发现也不例外。总之,达尔文的预言已经充分被证实了;因为从解剖学的角度而言,每发现一个较老的化石, 都愈来愈接近于猿猴。露西代表一种小型的人类,学名称为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生存于 300 万年前,已能像现代人一样直立行走,但其头骨极易被误认为黑猩猩的头骨。
这些验证工作的方法与达尔文时代并无二致,都透过骨骼的比较进行。但最近几十年来,已可利用更精密的技术来检验共同祖先的遗传理论。进化透过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变化,而脱氧核糖核酸又显示了不同种之间在生物化学和形态学方面的区别。组织比较是医师检查捐器官者的血液是否适合病人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测度种之间区别的方法。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愈密切,细胞的免疫结构就愈相似。分子生物学不仅可以用来估计种间的相关程度,而且可以用来测度两个种从共同祖先开始分化究竟经历了多久。
免疫分析和分子分析,已经厘清了人类、类人猿和猴子三者之间的关系。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两个种从 700 万年以前的共同祖先开始分道扬
镳。大猩猩开始从共同祖先分化出去的时间,还要往前推 200 万年。其他类人猿在时间和亲缘关系上与人类相距更远,更不要说猴子了。
根据达尔文的共同祖先理论,可以推断出一个同样的模式,而且已经在大量生命形式的无数次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根据比较解剖学,发现一种两亿年前可能属于温血爬虫类的两足动物,是恐龙和鸟类的共同祖先。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则有一种类似于哺乳类的爬虫类兽孔类(therap- sids)作为联系的纽带。25000 万年前,兽孔类曾主宰地球。
种群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最后都归结到细菌。细菌是人类迄今所知最老的化石,已在三十多亿年的古老化石中发现细菌的显微残骸。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生命都源于同一种原始生命形式的推想,在 DNA 中得到了最戏剧性的证实。用化学语言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样的。
达尔文对基因或 DNA 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想法十分不同凡响。直到克里克(Crick)和华森(Watson)在 50 年代破解了 DNA 分子的共同语言,重新发现了 19 世纪后期孟德尔(Gregor Mendel)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
实。
验证天择说
那么,进化论的天择说是否也已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呢?在某些方面看, 是的。选择意味着从多个候选者中挑出一个。从个体之间的遗传构成来说, 其基本的遗传组成是有变异性的。证实生物具有共同的祖先,也就证明了每一个生物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天择也意味着适应性。生物只有在本身的基因组合能最适应所处环境的生活方式(生物学家称之为小生境)时,才能有幸把它的基因传给后代。如果知道某种动物的小生境,我们就能预测该物种所能继承的特性。例如,一种易遭别种动物捕食的鸟类,若是雌雄鸟共同负责哺育幼鸟,它们的羽毛一定都不出色,静止不动时可完全隐藏在周遭环境中,天敌不易辨认出来。在进行孵蛋这类危险工作时,它们往往如此。至于那些羽毛鲜丽的鸟儿,因为在产卵和育雏的季节里更易遭到攻击,所以产雏较少。因此漂亮的鸟儿若非天敌甚少,便只有雄鸟色泽艳丽,而雄鸟不负责育雏。田野调查已经不止一次证实这种对鸟类和其他生物的预测。
漏洞百出
如果天择是进化的驱力,那么适应性就应当反应出环境变化。英国的胡椒蛾能够改变翅膀的色素基因,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最著名实例。若干年前, 大多数胡椒蛾的翅膀是灰白色的,主要模拟树皮的颜色,只有极少数个体为暗色翅膀。由于暗色翅膀与村皮的颜色相差甚远,易为它的天敌食蛾鸟类发现,故暗翅胡椒蛾数量极少。然而自从工厂烟灰的污染使树皮的颜色变成暗色后,浅色与暗色蛾子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几乎所有的胡椒蛾都变成了暗翅蛾,偶然可见极少数白翅的蛾子,但都已注定成为鸟类的盘中餐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出这样的实例,而且不胜枚举。它们似乎相当接近天择论的预言:适者生存。
但是,它们能否成为新种呢?达尔文明了,在一个类似于胡椒蛾之类的种群中,适应能力的变化并不等于物种的形成。因为种属的特性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对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已。形成新的物种,例如大猩猩与人科从某一共同的祖先分化成两个新的物种,是有条件的。由于某种原因, 一些个体可以发生不致影响该群体生存的非关键性变异。如果这些个体与其群体隔离,并独立地传宗接代,就可以演化成为新种。而且在新的环境中, 这些变异都可能成为影响其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看到了物种形成的实例。该群岛的每一个岛屿之间,都有广阔的水体分隔; 每一个岛屿的栖息条件都不尽相同。来自大陆种群的“难民”,诸如风暴带
来的幸存者,被孤立在新的环境中传宗接代。无论它们带有哪种有用的基因,又无论以后发生了哪些基因的有利变化,都必须有助于新环境的变迁所引起的适应性选择。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着许多种达尔文鸣鸟,每一种都适应于它的小生境,而且都是从同一个大陆种属演变而来的。
从物种形成的初步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又确定了一些隔离繁殖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所谓“性”选择了。雌性动物并非雄尽可夫,而往往会拒绝与某些雄性个体共同传宗接代。然而,这类物种形成机制的论证也引起了新的问题。达尔文和华莱士受到马尔萨斯思潮的影响,都从人口爆炸方面,发展到了物种的形成速度。生物过量繁育后代,若没有死亡速率的制约, 其数量势将持续增长,但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新物种才可能形成。在形成物种的机会较多的地方,例如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每种新的生物都要创造一种新的小生境。但是这种适应性的“楔子”似乎并不排斥它的同类,还在不断的以备种方式继续瓜分环境的资源总量,与达尔文的预言相反。
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与之类似。卡内基和洛克斐勒曾认为这种经济制度十分充分地反映了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的规律,其实汽车工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它自身在经济中的小生境,而且也为橡胶工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小生境。生物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种群内新物种的形成,也为另一个种群中新物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新植物的发展取决于食草动物新的适应性,而新食草动物的繁衍又取决于食肉动物新的适应性。共生演化现象,例如一种新的飞虫为一种新的花木传播花粉,是极为常见的。反之, 像是两种飞虫为了争夺一种花卉的花蜜而争斗,或者两种花卉为了争夺同一种花粉传播者而互不相容的竞争,却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这种生物个体卷入的斗争,实际上是与整个自然界的斗争。那些英国飞蛾相互之间并无争斗,它们的适应能力只与树皮的颜色和鸟的眼力相关。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许多科学家认为:达尔文天择理论的核心缺乏根据。演化的动力可能是自然选择,但是选择者并非竞争对手,新种的诞生也绝不是对老物种的死亡宣判。
灭绝现象不简单
这样看来,灭绝现象没有达尔文想的那么简单。以恐龙为例,如果达尔文关于生物为小生境而竞争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物种形成的速率将如他所料,与物种的灭绝达到完全的平衡。但是恐龙却在短时间内突然消失了; 迄今为止,从未在比马斯特里奇白坐新的地层中发现过恐龙化石。是哺乳动物杀死了恐龙吗?几乎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过。当时的哺乳动物都很小,它们的小生境与霸王龙或角龙之类并不相扰,当然也无力击败那些庞然大物。
所以我们该探究的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生存竞争。根据化石纪录和动物的选择性繁殖,达尔文深知生物的演化是非常缓慢的。
生物个体在生命期限内不能发生大的变化。比如说,一种生物无法因为气候日趋干旱而变成骆驼,只有在经历了许多代的干旱之后,生物才能忍受缺水的环境生存下来,或者形成某种防止失水的功能,并比无法办到的物种拥有某种繁殖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有某些生物个体灭绝。因为即使是现实环境中连续发生的缓慢变化,对生物的适应能力而言,也太迅速了。
但是,依事实看来,地质纪录也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演化速率。有一段时间是平静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物种保持不变,演化形成的新物种与灭绝的物种数量大致达到平衡。但是也有一些时期,物种形成速度极快,或者生物的灭绝更快。这些事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历史上存在着诸如恐龙灭绝那样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然后是一个间歇期。这时期生物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像兔子一样成倍地增长。然后分化形成新的物种。有时演化速度之快,谓之“爆炸”实非夸大其词。
如果我们注意到环境可能与上述生物演化形式有关的变化,那么就会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有趣联系。快速的环境变化,必将加速生物灭绝的速率, 使后者超过物种的形成速度。因为任何生物通过演化而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旧种属的灭绝与新种属形成所引起的竞争风马牛不相及。只说明生物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达尔文却反过来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有鉴于此,环境变化速率理应处于生物灭绝公式的核心地位。环境变化速率愈快,生物灭绝的速率也愈快。沿着这线索思考,近一个世纪来,古物学家四处挖掘所发现的奇珍异兽大规模灭绝,很可能是由环境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如果有一种灾变能够证明对这种或那种生物灭绝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达尔文的“规律”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鉴定古生物遗骸和现代物种的研究,预言何种生物将幸存,何种生物将灭绝,那么适者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预测结果是对适者生存说的最后检验。我们或许可以说,适应能力是判断幸存者的标准,定义适应能力为生物个体适应小生境的程度。从这个看法,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哪一种农作物具备从一场为时短暂的旱灾中幸存下来的能力。但是如果环境发生灾难性变化,我们能不能预言哪一种具备最快的适应能力?即使我们能够猜度未来灾变的情况,又能否预言即将产生的小生境情况呢?现在没有食草蛇类的小生境,因为根本不存在食草的蛇类。如果假设有一场灾变使啮齿动物和昆虫急剧减少,我们根据蛇的适应能力,仍难以预言它们能否靠藻类幸存下去,也无法预言经过几代的演化,它们能否有机会创造出一种小生境而不致灭绝。
由此可见,适者生存律可能并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据幸存者来定义适应能力,而没有独立的标准作为预言的基础。为一种那么邪恶的学说提供“科学”基础的所谓“自然律”,可能也是伪证。如果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诚然,控制生
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而非从劣等种族向优等种族的缓慢长征。可是达尔文的这种演化思想,在维多利亚则代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西方人的思想里。
科学家的体认
我不禁又想起了孩提时代遇到的矛盾。到我撰写本书时为止,我的生活可以分成属于三个国度的三等分。我在中国度过最初的 19 年;随后的 19 年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最近的 19 年住在瑞士。这三个国家各有其喜好的游戏。我认为,这些游戏可能反映了民族的性格或智慧。
中国人喜欢打麻将。这是一种适应能力的比赛。太过刚愎自用的人,不愿向必然规律低头,却往往会毁掉自己,痛失良机。而有的人却福至心灵, 屡屡取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它可以适用到每个人的头上。这与道教或者佛教的哲学一致。他们重视每一种生命形式或生活方式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由从天而降的机遇中受益。
美国人爱玩扑克。这是一种实力的比赛。人们可以靠虚张声势赢牌,但必须有足够的筹码。比赛的结果是强者为胜,这是美国方式。我在学生时代开始学习玩扑克,当时美国人对本身优越性的信念正受到严峻的考验。以达尔文的个体竞争和身价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为主体的西方哲学受到了围攻,但是对实力的信仰和对扑克的热爱都丝毫未受损害。
瑞士的国粹游戏叫做 Jass。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 1968 年 8 月 23 日所玩的一次 Jass。其时苏军正在向布拉格推进。一位瑞士的 Jass 能手与我为一方,我的妻子与一位美国人为另一方,后两者都是初出茅芦的新手。我们整晚都在旅馆里玩 Jass,窗外呼啸着枪声。也许是福至心灵吧,两位新手大获全胜。Jass 是一种赌运气的游戏,其胜负无法根据赛者技巧预卜。有人说,成为瑞士人是幸运的,但我却不以为然。我只能说,如果某人是瑞士人, 但愿他是幸运的。因为除非他碰巧出身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否则几乎无缘出人头地。
由此我悟出了三条不同的成功之路:一是成功属于自己,能掌握命运并压倒竞争对手的人;二是成功就是运气,谁也无法控制;三是成功属于那些能够忍辱负重的人;无论命运如何,都能因势利导,加以利用。因此,从扑克、Jass 到麻将,成功分别取决于实力、机遇和适应能力。我常想,三个十九年来,从不同角度受到的训练,开启了我的眼界,使我有能力判断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是否影响了我们对生命历史的观察。
我不希望断言我和我的邻居谁应在战争中幸存,也不希望预言谁的适应能力可确保他在核战中幸免于难,因此也不想对这三个国家的哲学妄论短长。相反的,作为科学家,我相信科学理论需要依据科学的资料及方法判断, 我判断的结果发现天择说绝非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偏见,而且是非常邪
恶的偏见。它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类清醒地领悟生命历史的能力,也影响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
本书将探讨研究最详的陆地灾变事件,和地质历史上生物大规模灭绝事件的证据,以便找出人类科学大厦中的那些不坚固的基石。我选择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着重于追踪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发现,探求这些发现对生物进化思潮的冲击。究竟是生存条件的争夺决定了恐龙的命运,还是来自外部的事件造成的环境变化引起了恐龙的灭绝?如果是灾变切断了有些生物连续演化的线索,其他生物为何能够幸存?我们可不可以说幸存者是适者呢?或者应该说,幸存者只是幸运儿?
